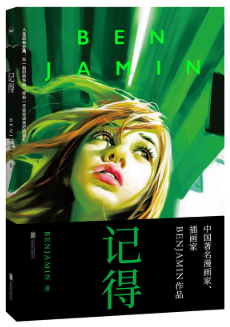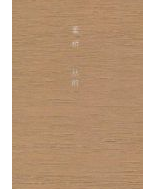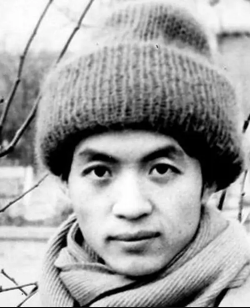橄榄香简介
《橄榄香》包含三十篇小说,每一篇都不长,字数控制在一千五到两千五之间。他说“情节要淡,情味要浓;记忆要远,念忆要近。”且看题目,《望江梅》,《梨花吟》,《紫薇园》,《鹤顶红》,《小寒碧斋》,都颇有张爱玲式的华丽与诗情。但张爱玲是“隔着几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,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儿凄凉”,董桥则不然,他从鹤顶红玉石扳指里也能闻到暗香袅袅,说到底,他回忆中的往事充满了温馨的情味。可能是文笔所致,他笔下的女子总是如同工笔画上的仕女,或是像旧式家庭里的闺秀或碧玉,带着一种恬静的个性和出世的气质。而他笔下的往事,风雨沧桑几十年,也恍如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,有着过去时代的韵律与风姿。
分享至: